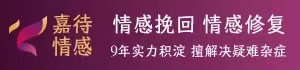新闻学院副教授:作为女儿,我第一次被允许独立“上族谱”

本文系刺猬公社X快手“还乡手记”非虚构故事大赛参选作品。作者甘丽华为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作者 | 甘丽华
2月2日,我有点迫不及待地回到家乡。前几年,春节不是在异国就是在他乡度过,今年我决定除了回家哪里都不去了。
我的家乡坐落在江西中部,隶属于近年来被宣传为“赣东望邑、理学名城”的崇仁县。县人民政府网站上写道:“崇仁自古崇教尚学,文风昌盛。”在这里,元代理学家、教育家吴澄,曾“折衷朱陆(朱熹与陆九渊)、独成一家”,创立了“草庐学派”。
但我出生成长的村庄其实和“望邑”、“名城”并无多大关系:八十来户人家、400余人口,不依山也不傍水,村前的一条小河从来就没有名字,离最近的市镇也有5公里之远。除两三户浙江移民外,全村人同属一姓。
今年迫切回家的重要原因还在于我想亲眼看看家里新修的小楼。在乏善可陈的2017年,唯一值得说道的事情大概就是和妹妹一起出资为父母在老家建造了一栋二层小楼。除了改善居住环境(如自来水、洗手间、热水淋浴等)的实际意义外,我们希望借此能多少弥补父亲没有生下儿子的遗憾。当然,历史、宗法、乡俗因无子而刻在父亲心上的伤痕,我们也许永远无法填平。

这种无子的遗憾和因此而来的内心的自卑是刻在我父亲骨子里的。我从小到大都能感知。重男轻女的这种压迫是历史的、宗法的,又是乡俗的。不一定天天缠绕着我和我们家,但一定在本质上塑造着我们。
在乡间,约定俗成的一些“特定”行当只交给那些没有生下儿子的人去做。比如“赶猪爷”,即赶着一头公猪,到家有母猪的乡民家里使母猪怀孕。父亲也曾经短暂从事过这一行当。我不知道这个风俗是如何形成的,但在我年少的心里本能地将之认定为一种羞辱。
有一次放学回家,在路上偶遇赶着“猪爷”的父亲,我羞愧得不敢认他。我的父亲当过兵、在林场任过职,是资深的老党员,会修理自行车,自学了简单电工,勤劳、和善、热情,培养了两位女博士,可以说是乡村能人,但他还是不得不面临这些无形的羞辱,只因他生下的是两个女儿。
这何尝不是刻在我心上的一道伤痕?在成长的过程中,我这个长女一直以“长子”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不仅自己从学习到工作丝毫不敢懈怠,还努力照顾父母、提携妹妹。
2015年,我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访学,旁听了一门博士生的质化研究方法课。上课期间我们需要完成好几次小组作业:以剧本的方式讨论诸如移民、性别、宗教、外交等社会问题。其中有一次小组作业的主题是高等教育,小组成员需要讲述各自上大学的故事。
其他同学给出的答案各异,一位白人学生是摩门教徒,他上大学的目的是寻求与上帝的对话;一位来自印度的学生则是为了逃出自己的家乡,获得自由;一位越南裔学生自上大学以来,一直在和家庭、社会针对亚裔学生的偏见斗争……
在由我完成的部分,我创造了一个想象的美国人,并试图给“他”讲述我父亲的故事。我问这个想象的美国人:“你怎么称呼你儿子的儿子?你又怎么称呼你女儿的儿子?”当然答案都是“grandson(孙子)”。我告诉“他”,但在我们中国人这里,前者是“孙子”,后者则是“外孙”;女儿并非真正的后代,而是别人家的人。
最后我说,我努力上大学的原因就是想告诉我父亲没有儿子没有关系,因为我就是他的“儿子”,我甚至比儿子更棒。念到最后一段,我在异国的土地上已是泪流满面。
一条小河从村庄的前面流过,我小的时候,夏季每天都在河里游泳。我和小伙伴特意选择水深堤高的地方,“噗通”一声跳入河水,然后一口气游到对岸。游泳技术不佳的我有一次差点被淹死,幸好被大孩子给救了回来。

但这条小河既承载着童年的快乐记忆,也深藏着我童年的噩梦。已经记不清楚那年我多大,但季节应该是冬季,河水变浅了,有些地方甚至露出了河底的砾石。不知怎么一大群人在河边围观着什么,还小声地讨论着什么。我挤进人群,朝人们目光所向望去,“她”一下跳入我的眼帘:小小的身体,裹着彩色的布条,搁浅在河滩上。
我看不到“她”的面容,这一模糊的形象却从此在我的头脑扎了根,并认定是“她”。这条小河时常会成为一些生命的最后归宿地,比如小猪仔、小狗、小鸟什么的,为什么“她”也会来到这里?
我还记得,围观的人群中有人朝“她”扔了一块石头,升腾起一丝白烟……所以一直持续很多年,“她”总会潜入我的梦:周围的一切都没有颜色,唯有“她”裹着彩色的布条,无声地躺在白色的河滩上,身体上空飘过几缕白烟。
2015年,中国青年报社曾对中国农村剩男现象进行调查。报道中提到,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曾一度高于120,是世界上最悬殊的出生性别比例之一。据专家推算,从1980年到2010年间,我国男性比女性多出大约3600万。此后,中国将经历长达几十年的“男性婚姻挤压”,1980年代后出生的男性中,将有10%至15%的人找不到或不能如期找到配偶。
“3600万”是个庞大的数字,对于普通人来说不一定具有实际的意义。但我能观察到的是,家乡娶媳妇的彩礼钱逐年升高,目前已经高达32万元人民币,而且还常常找不到合适的姑娘。人们或真或假地开始羡慕那些家里有几个女儿的家庭:彩礼钱到手,父母立即脱贫。而这足以改变人们的观念吗?
在我这次回到家乡的第四天,村里迎来了一件大事:“接谱”。所有甘氏家族子弟都在这天到家族总谱所在地——临近的丰城市迎接族谱。在外工作、打工的男性们大都回到家乡,参与这一近百年来“盛事”。
村里的男丁们凌晨3点钟就出发了,这几年打工收入提高、有些脑子灵活的人甚至开办了工厂,不少人是开着自己的小汽车去的。
接来族谱后,家族的男丁们手捧族谱、手持长香,敲锣打鼓地走过家族的每家每户。而每家每户都用震天的鞭炮来迎接那神圣的族谱。
在这次接谱中,我的父亲被委以重任——持长香,足见他在村里的人缘和威望。但我知道,他的心上始终有一个洞,谁也无法将之填平。这当然不是说父亲不爱我们两个女儿,相反他是极宠我们的。
我小的时候,不管是七月一日的党员大会还是八月一日的退伍军人聚会,他都会带着我去。即使在经济最困难的那几年,他也从未放弃,总是鼓励我们好好读书。
作为女儿,我当然不在受邀返乡之列。接谱这样的大事只有男丁才能参与,甚至当天中午聚餐的厨师也只能由男丁担任。
但变化总是有的。在这次修族谱中,女儿第一次被允许独立“上族谱”:以前的老谱里,女儿只会出现在其父亲的名下,新修的谱里,女儿也有独立的一栏,既介绍其“来处”—如其祖其父,也会说明其“去向”—嫁至何地何人,男女平等了。
“曾祖:呈柏,祖父:祥学,父亲:齐良。本世派名:四二世丽华昌。本人行传:齐良公长女,于一九七九年二月十日寅时生,博士学位,适河南南阳李氏。”看着族谱上属于我的这短短五十六字,心中突然有种莫名的触动。
除夕那天,家里的新楼挂上了一对红灯笼,楼上楼下、院内院外,对联贴了好几副,一派喜气洋洋。母亲念叨着:“你们两个为家里建了新房子,可是出名了。”父亲语言上没有表达什么,但我想他心里也是高兴的吧。
父亲,希望有一天,所谓的历史、宗法、乡俗能够真正地与您和解。也许到那时,我才能真正成为您的女儿,其间没有羞辱,没有遗憾,没有伤痕。

点击图片参与大赛
完

内容产业报道第一平台
微博 @刺猬公社
合作、转载事宜请联系微信号yunlugong
投稿邮箱ciweigongshe@126.com
网站www.ciweigongshe.net
关注公众号:拾黑(shiheibook)了解更多
[广告]赞助链接:
四季很好,只要有你,文娱排行榜:https://www.yaopaiming.com/
让资讯触达的更精准有趣:https://www.0xu.cn/
 关注网络尖刀微信公众号
关注网络尖刀微信公众号随时掌握互联网精彩
- 1 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 7904760
- 2 美军绝密报告曝光:介入台海必败 7808506
- 3 独居女子离世 无法用遗产购买墓地 7714490
- 4 中国玩具“玩转”全球大市场 7618543
- 5 “半江瑟瑟半江红”具象化了 7521101
- 6 海南封关:你的生活将这样改变 7424616
- 7 菲方人员持刀威胁中国海警画面公开 7327757
- 8 柬军士兵猛烈扫射 一只鸡意外抢镜 7232039
- 9 姚明女儿15岁身高1米9 英语超流利 7135964
- 10 全球航司为何排队来这里修飞机 7044373








 刺猬公社
刺猬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