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高铁上救人后反被要求登记信息
今年2月,一架从四川达州飞往福建泉州的航班上,一名61岁乘客突发昏迷,送医后不治身亡。
这件事在当时曾引起广泛讨论。有人提出疑问,这架载有上百名乘客的航班,真的没有一位医务人员吗?
航空公司回应称,乘务组在发现乘客无应答时,立即广播寻找医务人员,但始终无人回应。只能由乘务员按照程序为其吸氧、做心肺复苏,直到飞机落地,由地面医护人员接手。
家属对于航空公司的回应并不满意,事后发文,希望找到同机乘客,还原抢救经过。
乘客家属在社交平台发文寻人,希望还原经过
也有人从事后家属的态度中推测,如果当时有医生出面,那么他可能面临家属的指责和法律风险,有可能成为航空公司转嫁责任的对象,甚至称“幸好没有医生掺和进去”。
飞机、高铁上遇到突发状况,医生挺身而出,抢救生命,最终收获掌声与感激,这是以往常见的报道。但现实并不总是如此美好,与其他公共场合不同,在列车或航班中站出来的医务人员往往需要出示执业资质,全程被乘务员录像记录,事后还要留下姓名电话单位,甚至有可能面对家属追责带来的争议和纠纷。
于是,施救变得沉重。本该被鼓励的善意之举,成了一场权衡利弊后的风险决策。医生害怕义务救助后,责任被无限放大;乘务员也害怕流程疏漏后,被乘客投诉追责。原本该被鼓励的救人之举,逐渐变成了一场需要慎重权衡的风险决策。
“白大褂一脱,别人生死与我无关”,这句话,正在一些医生心中生根。因此,那些听到寻医广播后,在起身与沉默之间做出选择的人,他们的迟疑与克制,值得被探讨。
一次不舒服的见义勇为
去年五一假期,一趟京沪高铁列车上,广播突然响起一条求助信息:商务座有乘客突发意外,急需医生帮助。广播刚播完第一遍,车内一阵骚动。没买到票,只能在8号车厢过道蹲着的王德森——一名即将入职三甲医院的胸外科医生,迟疑了一会儿,没有上前。
“广播没说乘客病情,我只是名外科医生,万一去了帮不上忙,又耽误别的医生救治就不好了。”他想。
这是他迟疑的第一个理由。但远不止这些。
王德森快要博士毕业,五六年前已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也曾在120救护车上轮转过一段时间,接受过系统的急救训练。按理说,他具备足够的能力应对突发状况。但现实却让他多了一层顾虑。
“通常我的同事们遇到这种情况,都不太愿意救助,因为怕担责任”,王德森说,就连在三甲医院做行政工作的父亲也常劝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为他父亲的医院里有规定,如果有医生引发了负面舆情,即使本人没有责任,也可能被通报、扣绩效,甚至丢掉工作。
现实会让一些医生面对突发状况时产生顾虑/《问心》剧照
广播又响起了第二轮播报。王德森知道,列车上还没找到医生。出于医生的责任感,他决定先去看一眼。他从8号车厢一路穿过五六节车厢,最终在列车头部找到了那名乘客。
乘客被安顿在座位上,能说话、能喝水,没有晕厥、脸色煞白等典型症状,精神状态看起来很正常。现场围着三四名乘务人员和一个乘警,也没有表现出急切的神态。以他过往的急救经验判断,患者问题不大。他简单问诊了几句,得知对方年纪轻轻,患有慢性肾炎,当下感到“烧心”,没有明显疼痛,但一直怀疑自己有心脏疾病。
王德森帮他测了心率和血压,一切正常。初步判断是消化系统的问题,“跟心脏没有太大关系”。王德森说,“这种情况属于‘疑病症’——自己本身没什么病,但是疑神疑鬼地认为自己有病而造成的过度紧张。”他能做的主要是安抚情绪,告诉乘客可能是反流性食管炎,“下车后买点奥美拉唑吃就可以了”。乘客听完,明显松了口气,觉得身体好些了。
《谢谢你医生》剧照
真正让王德森感到“不愉快”的,是事后的操作流程。乘务员递来一张表格,要求他登记姓名、电话、工作单位,理由是:事后方便向单位内部汇报备份。他迟疑了一下,还是写了。
登记完,乘务员请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但王德森没有座位,他看到商务车厢很空,询问对方能否让自己暂时坐在这里,等来人了就走。乘务员客气地回绝道:“不好意思,我们有规定,不可以这样。”他没有多说什么,只能转身离开。
“我就又回到8号车厢中间,找了个角落蹲着……我也说不上来自己在不愉快什么,但从头到尾,整件事就让我挺不舒服的。”
现在回想起来,王德森还多了些后怕,自己当时留下了电话和工作单位。“万一后续患者真的出现心脏问题,会不会反过来追责到我,甚至追到我单位?”
“救人之后”的顾虑
王德森的担心不是空穴来风。几年前,曾出现过“救人反被告”的案例。
2017年,一名72岁的齐老太在药店突然晕厥,药店老板孙向波在对其进行心肺复苏时,压断了双侧12根肋骨。事后,齐老太将孙向波告上法庭,要求他支付近10万元的赔偿金。案件经过一审、二审和再审,最终在2021年,法院认定孙向波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一位法律相关人士汤诗诣告诉南风窗,法院如此判决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孙医生在紧急情况下自愿救助老太,其施救行为恰当,救治过程不存在过错。至于老太肋骨骨折,是对骨骼脆弱的老年人进行心肺复苏时难以避免的伤害。试想,若医生未施以援手,老太失去的很可能是生命;
二是自愿救助他人是美德,如果救助人因此承担责任将导致社会价值观没落,不利于激励医生进行院外救助,更不利于弘扬乐于助人的传统美德。
但和“扶不扶”一样,只要有一例诸如此类的诉讼发生,不管判决如何,造成的社会影响都是巨大的。
《好医生》剧照
中医学专业的研二学生熊熊,在网上也看过不少类似事件,其中有真有假,但这种担忧却存在。
去年7月,他在厦门开往漳州的动车上,救助了一位被铁制杯子砸到头的小孩。刚听到求助广播时,熊熊很犹豫,虽然他已经拿到了执业证,但“一个人有点怕”,直到看到同车厢有位阿姨起身,他才敢跟着一块过去。
到达现场后,他们给孩子做了脉搏、心率等简单查体,又检查了头部没有流血红肿情况,孩子也没有头晕头疼,“因为车上没有设备,所以无法进行其他检查”。情况暂时还可以,但他们也一直跟家长强调,“症状可能是迟发性的,不能因为查体正常就完全放心,下车后最好要完善头颅CT等检查”。
事后,乘务员让他们填写“旅客旁证材料”,其中包括姓名、身份证、工作单位、事情经过……熊熊犹豫不决,反倒是同行的阿姨拒绝得很坚决。她告诉乘务员,“我已经退休了,他还没毕业,我们能过去看就很不错了,而且买票都是实名制,想找人很容易,没必要再写这么多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
但依旧不断有乘务员前来劝说,一再强调这是流程需要,“陆陆续续交涉了20多分钟,最终还是没填,他们也没再强求”,熊熊说。
《手术直播间》剧照
后来,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导师,导师特意给他找来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二十七条也规定:国家鼓励医师积极参与公共交通工具等公共场所急救服务;医师因自愿实施急救造成受助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
熊熊明白,导师这是想告诉自己,碰到这种事不用怕,法律是支持医生去救助的。但他仍有担心:“说实话,法律保障是一方面,更大的问题是流程和人心。就算你做对了,如果有人揪着你,那后续要耗费的精力也很多。”
孙向波案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官司拖了4年,虽然最终赢得了清白,但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自己承受了经济和名誉上的双重打击,那种被纠缠的感觉让他很痛苦,药店生意也受到了影响,2019年就彻底关停了。
“我们不是怕救人,是怕‘救人之后’。”这是不少医生私下里的共识。
无奈的乘务员
关于“医生高铁救人”引发舆论风波的事件之一,是2019年发生在广西动车上的一幕。一名女医生在高铁救助患病乘客后,被列车员索要医师证,还被要求写情况说明书、签字画押。此事被新华社、央视新闻等媒体接连报道。南宁客运段发表致歉说明,称在处置过程中,未向医生做好沟通解释,造成了误解。
那一场公共讨论延续了许久,焦点集中在:医疗人员在院外施救,是否属于非法行医?万一日后产生纠纷,医生是否需要承担责任?铁路工作人员这种做法是否为了“转嫁风险”?
6年过去,这些争议没有消失,反而又在飞机上重演。今年1月23日,一名乘客在杭州飞往里斯本的航班上突发疾病。有医生及时出手救助,却在事后被航空公司要求出示执业证书。3天后,涉事航司回应称,这是“为还原事件经过所需的流程”。
航空公司要求医生出示执业证书/截图自红星新闻
汤诗诣认为,从法律层面上乘务员的行为是合理且必要的流程,“只有医学专业人士才有救助能力,乘务员查看医生资质是对乘客负责的表现。如果真出现违规致人受伤的情况,也有助于锁定责任人”。
解释看似合理,但在医生眼里,类似操作的信号很明确:如果你出手救人,就要准备好被全程录像、身份审查、责任追踪。这也是医务群体听到寻医广播时不敢起身的顾虑。
乘务人员的顾虑也和医生类似。面对突发情况,有一处细节没做到位,就会被投诉。“但这世上没有完美流程,如果有人想找事总能找得到。”一位在国内航空公司有五六年工作经验的乘务员小雯,给南风窗讲了两个在她们内部用来学习的案例:
有一次,一名乘客要求帮忙冲药,乘务员照做了,但因为没有把药泡开,事后被投诉“延误治疗”,旅客最终获得了赔偿;
还有一次,有乘客在飞机起飞阶段要水,乘务员等到飞行平稳后才送去,结果也被投诉。理由是“耽误了吃避孕药”,导致怀孕。
像小雯这样的乘务员早就接受过专业的急救培训,飞机上也配备了应急医疗箱、急救药箱等设施。如果乘客只是意外发生小的擦伤、烫伤,乘务员完全可以提供绷带或帮忙包扎;但涉及到用药、打针等医疗行为,他们一律不能动手,哪怕只是递一片晕机药,也要格外谨慎。
乘务员接受过专业的救急培训,在使用药物等方面也需格外谨慎/《向风而行》剧照
原因之一就是,乘务人员没有医疗资质,只能广播寻求有资质的医生,协助他们提供帮助。小雯说,只要航班上有医生响应广播,他们会第一时间请医生出示证件,全程记录施救过程,之后还要让医生签字、留下联系方式,证明一切是“依照医嘱操作”,万一有人投诉,他们能有证据自保。
这让乘务员和医生都陷入到了尴尬境地。遇到有人寻求帮助,出于善心,都想施以援手,可一旦涉及到追责问题,双方又有同样的顾虑,“有一个小小的毛病被人抓住,那就是全盘皆输”,最终受损的,是患者本身。
小雯说,假如某天没人响应寻医广播,乘务员只能尽最大能力提供基础服务和常规救助行为(如心肺复苏),其它“什么都做不了”。除非涉及生命安全的程度,飞机才会考虑紧急备降,但在大多数时候,飞机无法中断行程,患者只能熬到落地再说。
谁能来担责?
如果说在公共交通中,医生和乘务员的最大顾虑,是一不小心成了责任主体,那么,要想真正让他们无后顾之忧地施救,就必须在制度层面引入一个强有力的第三方保障机制。救人,不能只靠情怀和口号,更要让当事人心里清楚,一旦事情演变成纠纷,有人会为他们撑起法律和程序的防火墙。
小雯最近刚转到一家国外航空公司,她告诉南风窗,相比之下,外航在应对突发医疗情况时的流程更加清晰,也更有底气。如果旅客需要用药,只要简单确认对方是否有药物过敏史,就可以发放常用药品,包括退烧药、止痛片,甚至部分精神疾病用药。
这背后有一个关键的支撑点——地面医院的实时支持。小雯透露,大多数外航都与医院签有合作协议,一旦旅客出现身体不适,乘务员可以通过无线系统联系地面医生,由医生判断是否用药、用多少,乘务员照做即可。整个过程会被记录在案,不需要谁为判断失误单独负责,也没有人被迫“自证清白”。
大多数外航都与医院签有合作协议,一旦旅客出现身体不适,乘务员可以通过无线系统联系地面医生/《向风而行》剧照
相比之下,国内虽然也出台了相关法律保护施救者,但漏洞仍然存在。
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刘颖律师指出,如果救助行为存在“重大过失”,比如明显违反医学常识或操作错误,仍有可能面临赔偿责任。但所谓“重大过失”,在法律中并没有一个清晰、统一的定义。急救现场又往往混乱、条件有限,医生很难在事后完美复原当时的处置过程,一旦受助方事后反咬一口,医生将会陷入“有理说不清”的境地。
此外,目前我国法律对于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豁免规定也较模糊,一些细节地带存在争议,像退休医生、非本专业医生出手急救时,是否受到同等保护,也缺乏明确界定。
在这种背景下,施救者该如何自保?刘颖律师提了些建议,比如,在缺乏监控设备的场景,施救者可以用手机录音,记录患者的意识状态、呼吸情况及周围人的描述;并且邀请在场证人,用他们自己的手机拍摄施救过程,并留下联系方式;也可以借助“平安好医生”等第三方平台,实时上传救治记录,形成带时间戳的电子证据。此外,保留用过的药品安瓿、器械包装等物证,也有助于后续专业鉴定。
在刘颖看来,未来在制度保障上也应该进一步着手完善。比如,应该清楚地划定什么叫“重大过失”,把救人时的“合理行为”和“严重失误”区分开来。同时,还要设立反诬告机制,一旦有人恶意指控施救者,就必须承担惩罚性的赔偿责任,不能让医生在善意救人后被反咬一口。她还建议推行急救行为备案制,施救结束后,医生可以通过卫健委平台事后报备,作为将来举证的依据。
更重要的是,政府可以推广急救医疗责任保险,一旦出现争议,由保险兜底赔偿,最大限度减少医生和施救者的个人风险。
急救医疗责任保险的推广,在一定程度上能最大限度减少医生和施救者的个人风险/《谢谢你医生》剧照
在南风窗采访到的三位医务人员中,白雅茹是唯一一个不怕被事后纠缠的。她的底气,来自背后强有力的官方后盾。她出身军医家庭,自己也是转业军人,目前在一家三甲部队医院任护理督导专家。她说:“我们医院从来不会因为舆论去处罚医生,反而会第一时间出来保护我们。对于在任何场所勇于站出来救助病患的医护人员,医院都是鼓励和支持的。”
不过,即便是白雅茹,也曾有过不愉快的救人经历。大约七八年前,她在西安前往西宁的高铁上,遇到一位乘客小腿被车门划伤,伤口约8-10厘米长,血顺着腿往下流。当时列车上没有缝合工具,她只能用产妇急救包进行清洗、消毒和包扎,好在距离到站时间并不长,她就建议乘客下站后找医院进一步处理。
原以为事情到此结束,没想到之后列车员又要她填了一堆表格,还按了手印。“我很反感那个红手印,就像你做了什么错事一样。”她说,“我愿意帮忙,但不想被这样对待。从头到尾没有一句感谢,只有乘客说了句‘谢谢’。”
她理解列车方需要流程,但难以接受那种冷漠的态度。“你可以拍视频、留证据,但应该告诉我为什么这么做。整个过程只感觉到乘务员担心背锅,生怕万一有责任扛到自己身上。”
即便如此,白雅茹仍然坚持,如果将来再遇到类似情况,她依然会挺身而出。但不是每一个医生都像白雅茹一样,有一个强大的后盾为她保驾护航。更多人,在公共场合伸出援手之前,会先问一句:值不值得?万一呢?
网络审视下的不安
这种犹豫,除了责任制度的缺位,更与近年来在社交媒体上被无限放大的医患矛盾息息相关。医生不只是医生,他们成了随时可能被围观的公众人物。一旦卷入突发事件,手机镜头往往比急救箱更快到场,而网络判断也常常快于专业诊断。
“医生最怕的不是施救,而是被拿放大镜检视,最终上升为公共事件。”王德森告诉南风窗,即便在医院里,医生也不敢保证万无一失,出错是医疗工作的一部分。
比如操作中不小心损伤一根血管,或者大型手术中局部止血时多出100毫升的血,这些情况在专业上都是可控、可补救的,不会造成后遗症。但如果放到网络上,“不完美”就会被放大成“失职”,被渲染成耸动的公共舆论事件。
即便在医院里,医生也不敢保证万无一失/《问心》剧照
公共空间的情况更加复杂。高铁车厢、飞机通道、马路边,既没有配套的医疗设施,也没有完整的抢救空间。医生在这种场景中施救,只能依靠临场经验和条件反应,但围观者和网络却往往要求医生做到“标准化施救”。
有人因为撕破病人衣服做心肺复苏,被要求赔偿衣物;有人因为没有“先摸颈动脉再按压胸口”,被质疑专业不合格;还有医生在海边身穿泳衣抢救溺水者,被人造黄谣,贴上“不要脸”的标签。哪怕最终被媒体辟谣澄清,这段经历对施救者而言,也是一场身心俱疲的风暴。
这是一种荒谬却真实的处境:救,可能付出声誉、时间、金钱甚至法律上的代价;不救,却无须承担任何责任。医生要在这两者间,反复权衡、犹豫、掂量。就算不救,也不会有人责备。“白大褂一脱,别人生死与我无关”,这句话在医生群体中反复被提及,正是多年防卫与受伤后的自我告诫。
这种对“救”与“不救”的犹豫,不仅是医生的困境,更是一个社会信任滑坡的缩影。医生不信任患者和乘务员,乘务员不信任医生和患者,乘客也未必信任自称“专业人士”的他人。人们在互相防备,生怕自己成为下一个被指责的对象。责任在这个多方交错的结构中,成了一把没人敢接的刀。
责任在这个多方交错的结构中,成了一把没人敢接的刀/《疼痛难免》剧照
而制度保护与社会舆论的缺席,也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这种“逃避式自保”。人们习惯把医生塑造成无私的“服务者”,却忽略了他们首先是普通人,会恐惧、会焦虑、也会自我保护。如果“救人”变成了一场风险极高的社会赌博,最终只会把原本愿意挺身而出的人,逼退回人群。
值得庆幸的是,仍然有医生愿意救人,只是他们的方式,正在悄悄变化。
熊熊说,自己今后再遇到类似情况,还是会很犹豫,“可能先远远看一眼”,如果判断自己有把握成功,再去上前。平时出门旅游时,他也会在包里常备几根针,要是遇上突然晕倒的人,就可以针灸急救。现在更多时候,这些针被用在旅途中,帮那些和他聊得来的游客们“扎两针养养生”。
这是他表达善意的另一种方式——在不引人注目的时刻,在被允许的范围内,温柔地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
那双愿意施救的手,并没有完全收回去,只是学会了更安静地存在。
(应受访者要求,王德森、熊熊、小雯和白雅茹为化名)
文中配图部分来源于网络
作者 | 乔悦
编辑 | 苏米
值班主编 | 吴擎
排版 | 菲菲
关注公众号:拾黑(shiheibook)了解更多
[广告]赞助链接:
四季很好,只要有你,文娱排行榜:https://www.yaopaiming.com/
让资讯触达的更精准有趣:https://www.0xu.cn/
 关注网络尖刀微信公众号
关注网络尖刀微信公众号随时掌握互联网精彩
- 1 习近平同马克龙交流互动的经典瞬间 7904097
- 2 黑龙江水库冰面下现13匹冰冻马 7807943
- 3 微信表情包戒烟再度翻红 7711854
- 4 2025你的消费习惯“更新”了吗 7616270
- 5 三星堆与秦始皇帝陵竟有联系 7523097
- 6 为啥今年流感如此厉害 7425351
- 7 劲酒如何成了年轻女性的神仙水 7330278
- 8 中美合拍《我的哪吒与变形金刚》首播 7232284
- 9 女子裤子内藏2斤多活虫入境被查 7138249
- 10 中疾控流感防治七问七答 70394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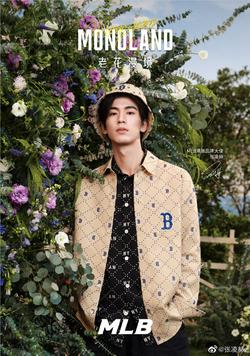


 是非题
是非题







